张 琳
张大复,字元长,江苏昆山人,著作甚富,以《梅花草堂笔谈》闻名于世。全书十四卷,内容上自帝王卿相,下至士庶僧侣,树木花草,飞禽走兽,尘世梦境,春夏秋冬,皆在笔谈之内,是他艺术世界中最耀眼的部分,余每每读来,皆回味无穷,仿佛走进一隅休憩心灵的桃花源。
“一卷书,一尘尾,一壶茶,一盆果,一重裘,一单绮,一奚奴,一骏马,一溪云,一潭水,一庭花,一林雪,一曲房,一竹榻,一枕梦,一爱妾,一片石,一轮月,逍遥三十年,然后一芒鞋,一斗笠,一竹杖,一破衲,到处名山,随缘福地,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。”人生几度诗意,不过诗酒茶花。诸多妙物,相信当时贫病交加的张大复并不曾拥有,可他在自己富足又自由的精神世界中流连忘返。他对理想生活的向往、欲回归山林泉石、怡情乐居的渴望、率真自然的内在意趣,恬淡自适的人生追求,是四百年后的我依旧向往的生活。
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而今,隔着四百载风雨后的月下之夜,凭借薄薄的书册,余以窥得先贤对人生有限、宇宙无穷的感叹,领略古人的风雅。“邵茂奇有言:天上月色能移世界,果然,故夫山石泉涧,梵刹园亭,屋庐竹树,种种常见之物,月照之则深,蒙之则净;金碧之彩,披之则醇;惨悴之容,承之则奇;浅深浓淡之色,按之望之,则屡易而不可了。”人在月下,不期然间被染上淡淡的离愁,便可以把心中的情感寄托于迷离的月色之上。三五好友作陪,信步庭中,草木生长,破山僧舍在月光的笼罩下,多了一层婆娑的光影之美,也变得可爱起来。在淡云微月的感染下,寄情山水间,在自然中寻求抚慰与拯救,湖上泛舟,赏景赏心,因月色而忘我,当有不同之韵味。
苦难的生活里,也有点滴美意。“一鸠呼雨,修篁静立,茗碗时供,野芳暗度。又有两鸟咿嘤林外,均节天成。童子倚炉触屏,忽鼾忽止。念既虚闲,室复幽旷,无事坐此,长如小年。”张大复半生与疾病相伴,伤寒、肺炎、心悸、偏头痛以及失明,在饱受疾病摧残下,他并不消沉,自诩的给自己取斋号为“病居士”,名其庵曰息。养病的日子里,老屋药气蒸鼻,蚊蚋撩乱窗间,看不见反而让听觉和触觉愈发灵敏起来。拥炉静坐,茶吊中的沸水翏翏如松风响,不雨的三月,井水仿佛甘露一般,昏然欲睡间,儿子郎朗书声,令他心颇乐之。家徒四壁的他有着富足的精神世界,疾病缠身,然不失风雅,他在沉静中思索,在友人们的探访中发出喟叹,饮酒赋诗、焚香啜茗,口述著书,虽不能以康健之躯体仗行天涯,却意游万仞,胸中释然,他心中那清澈高远的世界,化为品泉、言志、试茶、论交之小文,令人为之动容。
“烧笋午食,抛卷暂卧,便与王摩诘、苏子瞻对面纵谈”。他的朋友中,达官显贵并不多,与许多耀眼先贤的书信里,流露出几许洒脱,存几分哀怨。终究是多病之人,“木之有瘿,石之有鸜鹆眼,皆病也。然是二物者,卒以此见贵于世。非世人之贵病也,病则奇,奇则至,至则传。天随生有言:木病而后怪,不怪不能传其形。文病而后奇,不奇不能骇于俗”,“天下之病者少,而不病者多。多者,吾不能与为友,将从其少者观之。”噢,文章病了才能不同凡响,天下患病的少,不患病的多,我不能与多数人成为友人,还是从少数人里获得感悟吧。一缕清高的文人之气呼之欲出。一句“敬问天公,肯于方便否?”吾不由得感慨,他心里的苦楚,唯有在一饮而尽的相邀中,在百转千回的昆曲里,方可短暂消弭罢。
文以载道,我们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汲取精神力量,那些读书治园、斫琴制墨、临帖刻石、卧眠听雨的闲雅生活;那场1600多年前的曲水流觞;那东晋时期曹植在恍惚之际睹洛神的惊鸿一瞥,在文字的记载中长存,瞬间永恒,亦成就了时代的风华。古人的洞见,如同颤巍巍的墨滴,无声入水,如烟袅袅,幻形而生。一锭墨,于砚中轻研细磨,浓淡之间,含五色合三才,让历经千年的文字,依旧黑亮如新。
人生中总有许多世事纷扰,囿于斗室,沉溺手机、电脑无法自拔之际,也得多一些闲情雅致,偶尔抽身事外,择一好书,随心而读;又或寻幽探胜,于自然间纾解忧怀;松花酿酒,春水煎茶,在一盏茶汤中照见自己,品悟人生的意义。
阖上书,脑海中浮现一捋银髯、一身傲骨的老叟,穿透厚厚的光阴,迎面而来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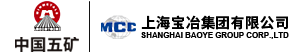
.png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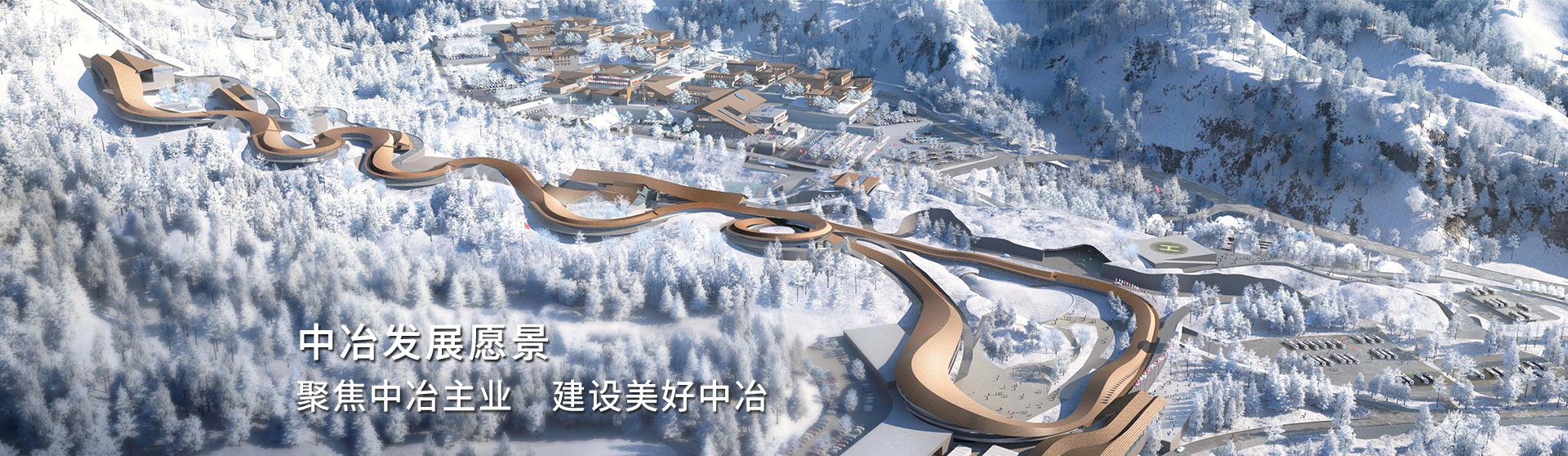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.png)